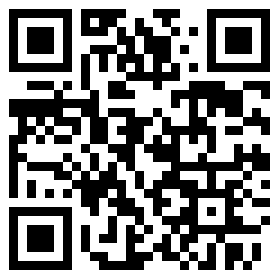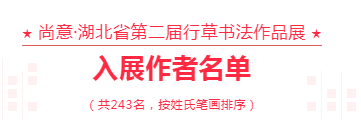0/500
2023第三届中国当代研究型书画家“笔法研究” 专题学术研讨会纪要(一)
2023/06/09 来源:书法报·书画天地 责任编辑:刘娟 作者名称:;
2023第三届中国当代研究型书法家“笔法研究”专题学术研讨会纪要(一)
编者按:
中国当代研究型书画家团队自2013年8月成立以来,在洪亮导师的带领下,着力于书画笔法之研究,卓有成效。团队先后在浙江杭州、山东龙口成功举办了2015中国当代研究型书法家“笔法研究”专题学术研讨会、2017中国当代研究型书法家“笔法研究”专题学术研讨会。值2023年中国当代研究型书画家团队成立十周年之际,由洪亮工作室书学研究会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当代研究型书法家“笔法研究”专题学术研讨会暨团队成立十周年书画篆刻和学术成果展5月20日至23日在辽宁朝阳举行。期间,召开的“笔法研究”专题学术研讨会为本次活动之重点,绽放出诸多学术火花。现根据现场专家发言、相关专家的书面发言稿分类整理纪要,以飨读者。


洪 亮(九三学社中央书画院副院长、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研究员、中国当代研究型书画家团队导师):我们团队先后在浙江杭州、山东龙口成功举办了2015、2017中国当代研究型书法家“笔法研究”专题学术研讨会。这两次“笔法研究”专题研讨会围绕喻指性笔法,如:锥画沙、屋漏痕、印印泥等;实指性笔法,如:提、按、顿、挫、入锋、出锋、实逆、空逆、实回、空回、转锋、折锋、驻锋等具体的笔法动作和形态展开充分的讨论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在我们已出版的《经典碑帖笔法临析大全》(48本)和《中国历代书论研究丛书》(13本)中都有呈现。
本次“笔法研究”专题学术研讨会可对上两次研讨会尚未完成的任务继续进行研讨,同时,也可对“书法笔法与笔法的艺术表现”这个困扰书法界数百年的学术问题进行讨论与研究。元代赵孟頫提出:“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中“用笔千古不易”也倍受争议。究其根源是后人将“书法笔法与笔法的艺术表现”两个概念混为一谈所致。书法的笔法是指书法用笔的基本形态及其规律(原理),当然是千古不易的。而书法笔法的艺术表现则因人因时因地而变,并且是千变万化的。有了这个基本认识,我们这次“笔法研究”专题学术研讨会的选题就大大拓展了。我想可以从“字体、书体笔法个案研究”“字体、书体笔法比较研究”“书家笔法个案研究”“书家笔法比较研究”“书画笔法原理及笔法艺术表现形式”等五个方面打开思路、展开讨论,每位团队成员根据自己的擅长来确定选题进行发言,一定要切中要害,文字精练,言之有物。
字体、书体笔法个案研究
吕为民(中国当代研究型书画家团队成员):《好大王碑》通篇书法气势恢弘,浑厚雄强,笔法圆劲而蕴含篆意,结体方正、拙朴。线条看似简单,其实对线条的质感和用笔的变化要求非常高,用笔的节奏感很强。其笔法看似简单,然而长线条“绞笔”丰富,充分体现出线条凝练和遒劲。通篇作品很平实但不呆滞,波折不明显,用笔收放自如,天真烂漫,在平淡中又蕴含着古雅和灵动。《好大王碑》入笔无论逆锋还是折锋,均求圆润,笔笔中锋,没有“蚕头雁尾”。隶书一般扁平居多,而此碑偶尔略显纵势,以隶为形,以篆用笔。结字方拙,没有大开大合的用笔,笔画始终保持在方格内,但内部结构变化多端,打破平衡格局。通篇布局平正统一,虽每字独立,但上下呼应,左右和谐,行距略紧,上下字距适当拉开,又因字体大小错落,线条粗细变化,左右挤压,字字玉润珠圆,自然而雍容,通篇充满张力。此碑笔法无刻意造作之态,没有明显的波挑,中锋卧笔,线条质感丰富。如果只求圆稳而忽略线条质感,就得不到此碑的灵动宕逸气韵。如果只求灵动而忽视卧笔,就会失去此碑的“雍容典雅”。

冯会明(中国当代研究型书画家团队成员):我最近在临习汉碑《封龙山碑》,感觉到其用笔是“以篆入隶”,圆转遒劲,极富篆意。此碑虽偶有方笔,但以圆笔为主,用笔圆笔中锋,锋芒内敛而奔放,极富篆书意趣,因此突出地表现出宽博、豪放、雄肆的美感。笔法近《石门颂》,但不同的是转折处的处理,《石门颂》是提笔暗过,而此碑则翻笔直下。此碑篆籀之法通灵,如“口”字旁、“石”字旁和“望、韦、举、与、光、物、刻、铭、富”等字都是以篆入隶的代表,起、承、转、合、收,干净利索,如踏雪无痕,似鸿鹄羽翔。故其能将浑厚奔放、劲挺秀逸、宽松圆润寓于一体,而给人以高古超逸的审美感受。逆锋入笔、回锋收笔写出的线条不仅能在感觉上增强人们对力感的体验,还会加强人们对厚重感的体察。《封龙山碑》用笔的篆籀之气,向我们揭示了其线条的力感之美。其行笔不激不厉、缓缓而来、徐徐生发、从容自信,蕴含一种内敛之力,显示一种安然之态。
章志高(中国当代研究型书画家团队成员):虞世南的代表作《孔子庙堂碑》,因是碑刻传世,所以临习此碑要透过刀痕看笔锋,其笔锋内敛、含蓄,笔画俊朗圆润,沉重稳健。比如它的横画,起笔用尖锋或空逆落笔,落笔即折,一折而笔毫齐正,中锋运行,收笔略按回锋,牵引下一笔,动作十分清晰,干净利落。粗看笔画粗细变化不是十分明显,只有在自然运笔中见细微变化,感觉动作极致简练,但不简单。再如横折至折处笔锋稍提,再向右下角轻轻一按,用转笔法向左下或向下写直画,如“而、闻”;有的笔画至转弯处轻盈提起暗过,如“乃”的第二折。点画大多呈右向点,起笔尖而收笔圆;捺画前半部分特别长,捺脚厚实遒劲,斜捺入笔速度快,形成虚实之势,行笔倾斜角度也非常大,与“撇”搭配时,往往撇短捺长,笔力异常坚挺。平捺有空逆、实逆,空逆以切入为主,实逆起笔较圆,行笔从视觉上给人感觉平稳、浑圆、舒展,有力量感,一波三折明显。钩画短而坚劲,有的带有隶书状,如“事、手、子”等,其次,有些主笔(如长横、长撇、长竖、戈钩等)尽力展开,给人开阔、舒朗的感觉。总之,此碑用笔相当精致,水准很高,要领悟其中的用笔方法和精神状态,需要不断地分析、研究、探讨,在反复临摹中思索、体会。

陈荣全(中国当代研究型书画家团队成员):我谈谈张旭《古诗四帖》的绞锋笔法。《古诗四帖》整个书写过程始终都是以手腕为轴心的多方向绞转,用笔是以手腕为中心用力点,手指是辅助对变化着的笔锋进行调整,并以微小的指部动作拈管,根据笔锋变化旋转笔杆,让笔杆力量传递到笔锋,使笔锋一直保持在包裹(裹锋)状态下进行书写。这种书写笔法成为了一些笔法理论的源头,是值得书法爱好者们认真学习和研究的。

李庆博(中国当代研究型书画家团队成员):《张迁碑》以朴厚劲秀、方整多变之态,被公认为传世汉碑中风格雄强的典型之作,爱慕者众多。其笔法艺术表现,因多变而疑似多人合成。碑刻艺术的风格基调是源自书者,定于刻者。文书上石后,石刻或许是几名工匠或师徒凿制,固有了非一字定统篇之规的“方整多变”,字体有大小,笔势多变化,有的字看起来似乎变化得有些夸张。如“兴”字最后的两画,夸张得集靠一边,一时险情顿起,似有不堪承重之妙;又如上下结构的“忠”字,偏离上下中心线,笔法艺术效果稚气十足;再如“令”字,上部“人”字的一撇,笔锋骤停或突逆回锋,犹如神来之笔,盘活一片,立显灵动,妙趣横生。通篇雄壮拙朴,活而不滞。由此说明,书法笔法艺术表现是因人因地因时而变,受诸多因素影响的。上述例字笔法有的看似“败笔”,却恰恰成了难以模仿和超越的别具神采之处。常有感叹说依此创作难,我认为一味放大其横竖撇捺的一般特点,以及程式化地摹创是一个重要原因,忽视了其笔法字法及章法等非主流形态衬托,临创作品多是千人一面,成了再加工的同款产品,失去了原有的底蕴。临摹《张迁碑》,有规则也无规则,宜抓基本特征,重在艺术表现,于欲求非求、似醉意醒中整体学创。
字体、书体笔法比较研究
洪明祥(安徽省绩溪县书协副主席):我谈谈《鲜于璜碑》与《张迁碑》的笔法对比研究。两碑在用笔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其雄强朴茂风格都是通过方笔来体现的,大部分字体是横画粗重,下笔力按厚重,方起笔,逆势铺毫,行笔粗壮有力,笔画厚实,收笔方起,体现古拙,也有用绞转笔法,突出朴茂风格。两碑的竖线大部分上竖轻灵迅疾,下竖粗短而有力,收笔方整,体现古朴;撇画皆先竖后横,中锋涩行推出,捺画在许多雁尾处理上讲究厚重,先重按稍顿轻提,或重按转笔上提,突出雁尾的丰富性。两碑字体在笔画搭接处也注重内方,点的笔画特征以三角形方点为主,但也常用小圆点,用笔轻盈灵动,很有艺术魅力。当然,两碑在用笔上也有不少差异,《鲜于璜碑》雄强整饬,厚重端庄,方笔为主格调,横画起笔方整宽厚敦实,行笔可铺毫亦可绞转,收笔常有雁尾,需要厚实重按轻提。《张迁碑》横画行笔或铺毫静行,或略有提按律动,收笔顺势提笔,或驻笔上提,收笔更讲究随性等。总之,《鲜于璜碑》强调规整和端庄,用笔方整中显古意,点画灵动中显朴美,形成了该碑独有的规整朴美风格。《张迁碑》雄强朴茂,用笔注重古拙和雅趣,在拙笨中显稚意,体现经典碑帖的“拙美”艺术风格。
洪 震(中国书协会员、中国当代研究型书画家团队成员):我的发言主题是《张迁碑》与《礼器碑》笔法表现比较研究。《张迁碑》落笔稳重,运笔劲折,粗细相间,变化微妙。直曲结合,方劲沉着。笔法由圆变方,是汉隶方笔系统的代表作。起笔方折宽厚,转角处方圆兼备,行笔阔笔直书,力感表现极为强烈,使得线条极具抒情性。用笔铺毫、裹绞相结合,其线条质感老辣坚实,蕴藏丰富,积点成线,一点一画皆是情感表现的载体。再加上其结体奇崛,时而头大身小,重心下移,左右不均,错落揖让,形成此碑方正古拙,质朴雄强的风格特点,堪称神品。《礼器碑》的书风细劲而雄健,端严而俊逸。碑阳后半部分及碑侧、碑阴是其中最精彩的部分,用笔灵活多变,笔法极为丰富,故清人王澍称该碑“瘦劲如铁,变化若龙,一字一奇,不可端倪”。该碑蚕头雁尾的表现手法丰富多样,主笔副笔的粗细、长短,对比表现悬殊,变化十分明显,超越正常的想象,而且一个主笔之中的变化也极为丰富。其用笔规律为:中锋为主,中侧互用;以提为主,提按结合;用笔爽健,细而不弱;俯仰同在,向背相生。相较而言,《礼器碑》代表“今妍”的范畴,作为汉隶入门学习的最佳范本,能“登堂”;《张迁碑》则代表“古质”的范畴,学习此碑能“入室”。
金舒年(北京大学教授):我们学习隶书选择范本的时候,主要是从汉碑隶书、汉简隶书、清代隶书这三大系入手。这些隶书的笔法虽然都讲究蚕头燕尾,逆起驻收,一波三伏,但细节上却大有不同。这个“细节”大到如何运笔,小到笔尖的一个轻微抖动。
我记得自己在父亲的指导下最早临习隶书,就是从汉碑隶书开始的。《曹全碑》笔法的清秀灵动、润泽优美是最容易吸引年轻初学者的目光的,但那时候关注的仅仅是隶书扁阔的外形和那微微翘起的“燕尾”。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感觉这种清秀灵动的风格已经不足以承载此时的心灵律动和内心感悟,而《石门颂》笔法的粗犷、厚重和深刻则似乎更加能够跟自己的内心和胸怀契合。
从笔法上看,《石门颂》有《孔宙碑》的左舒右展,有《史晨碑》的方正庄重,也有《曹全碑》的规整,隶书的其他法则也体现得很完备。而且此碑同《乙瑛碑》一样,笔法风格很有骨感。个人觉得学书如做人,需要先立骨,有了骨干,再去追求细节。但可惜的是《石门颂》原帖比较斑驳,模糊处较多,不利于临习,因此我选择了清人何绍基临的《石门颂》,相对而言比较清晰,便于临习。而且何绍基在临习的基础上融入了个人的感受和创造,他的隶书笔法既有石刻的粗犷厚重,又有清人隶书的秀气雅致,很有艺术美感。
彭庆阳(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研究型书画家团队成员):我谈一下书写材料对笔法艺术表现形式的影响。近年来我一直在撰写湖州书画史,注意到米芾的《苕溪诗帖》《蜀素帖》两件作品的书写内容都和湖州有关,且书写时间前后也只是相差月余。二者的艺术风格都是以和谐多变为准则,以率真自然为旨归,用笔“八面出锋”,宕逸而精致,皆能体现米芾“刷”字的意味。但由于书写材料、书写状态的不同,其书法笔法的艺术表现也是有变化和差异的。
《苕溪诗帖》在用笔上是中锋直下,正有“刷字”之妙;行笔上提下按、起伏明显,落笔迅疾,从而浓纤兼出,笔画呈现出粗细反差较大的视觉感,且结字“不作正局”,跌宕多姿,而笔势纵横恣肆,如“风樯阵马,沉着痛快”,从而使通篇书风率真自然、痛快淋漓、变化有致、逸趣盎然。而《蜀素帖》由于书写材质是绢,不是《苕溪诗帖》那种澄心堂纸,且这种绢为蜀素,“坚白缜密”而略显粗糙,行笔其上,滞涩难行,同时由于丝材质的排水性,故不易受墨,即使下笔全力以赴,也会出现较多的枯笔,形成“筋胜”之书写特性。因此《蜀素帖》在用笔上没有《苕溪诗帖》的跳跃性那么强,但却“如狮子搏象,以全力赴之”。
正是二者用笔存在差异性,故各展其姿、面目迥异,但皆是米芾“精神笔力毫发毕备”的精品之作。
书家笔法个案研究
刘品成(北京洪亮书画艺术馆馆长、中国当代研究型书画家团队成员):我的发言主题是“笔端有情任纵横——浅谈《祭侄文稿》抒情性笔法的经典表达”。
书法创作之难,最难莫过于抒情。《祭侄文稿》之所以辉耀千古,正在于作品中所蕴含的巨大情感力量。而这种情感力量是通过独具个性、富有生命力的笔法得以充分激发和彰显的。将爱与恨、悲与愤、血与泪凝于笔端,纵情奔放,自然天成。
遒劲的篆籀笔法深刻地表达了书者痛彻心骨的思想情感。作品以圆笔中锋为主,笔锋内含,藏锋出之。厚重处浑朴苍穆,细劲处筋骨凝练,转折处变换精巧,连绵处笔圆意重。外拓圆笔纵情挥毫,作者的情感充分抒展。线条浑厚圆劲,富有立体感。间杂楷隶,奇趣迭出。圆润、浑厚的笔致和凝练遒劲的篆籀线条,不仅展现了颜真卿用笔上非凡的艺术功力,而且为情感的抒发奠定了坚实基础。
迅疾与徐缓的运笔,真切反映了书者内心情绪的起伏变化。行笔忽慢忽快,时疾时徐,欲行又止,可见书者为文始末思绪起伏、血泪交织、悲愤交加。文起运笔舒缓,人平字稳;文中渐起波澜,有大量字画涂抹,难掩丧侄之痛;行至末尾几行,由行变草,运笔迅疾,跌宕起伏,一泻千里,非快速行笔不足以表达激愤之情。
果断与畅达的行笔,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爱憎分明的正义凛然。用笔沉着果断,迅速利落,杀笔狠重,戛然而止,唯如此方能抒发痛失亲人的大悲、对称兵犯顺者的极愤之情。
枯涩与自然的渴笔,强烈地抒发了书者撕心裂肺的悲恸情感。“将浓遂枯,带燥方润”的渴笔枯墨时有出现,笔力沧桑老辣,墨黑处见稳重,露白处显空灵,墨色由浓而渴,造成虚实、轻重、黑白之间的节奏变化,反差对比强烈,作者的情绪在书写节奏中尽数流露,更迸发出对叛贼的痛恨之情。
郑和新(中国书协会员、中国当代研究型书画家团队成员):我曾数次临习孙过庭《书谱》,感觉其用笔虽然变化丰富,但由于字数多而结字不易变化,再加上其执笔的局限性,使其点、横、竖、撇、捺等笔画书写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如上部左点一般先向左疾顿后迅速往右上折锋而出,形成一个顿折笔法,主要是为了与右边的点或点撇构成呼应,而右边的点撇或短点恰恰是左点的延续或收笔,这两点的距离也常常拉得很开。特别是这种组合出现在字的下部,右点作为该字的最后收笔,或按或顿或出,形态多姿。右下点的收笔也往往是下一字的起笔,所以常常往左撇出。横画起笔如承上则有牵丝露头,若无承上则切笔入纸,多为方笔,或轻或重,入笔角度或大或小,不一而足。横画收笔或下带,或上翻,视其所需;竖的起笔大多顺锋而下,有右倾有左欹有中泻,大多露锋在外,留下圭角,侧锋行笔。竖的起笔逆锋较少,一露锋入笔往右轻顿后便直泻而下,有长驱直入之势。长撇往往入笔轻按,往左下疾速而行,有弧度,至收笔处又疾顿,不使失逸无度,有的往往回锋再去写下一笔,不回锋时弧形而出,潇洒而且苍茫;长捺承撇画余势连带起笔,由轻到重再轻提,或重按再提笔右拉,由重至轻而收。

何昌廉(浙江省书协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当代研究型书画家团队成员):纵观黄庭坚书法,其笔法的表现性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笔法的形态表现多样。每个基本笔画都有很丰富的写法,如横画运笔注重起笔和收笔,往往重起重收,而且运笔线条很讲究提按轻重的转换变化,有的甚至中间故意断笔,形成笔断意连的形态,增强笔画的韵律感和节奏感。同一个字的写法也讲究变化,绝不雷同,如草书“璧”字有多达三十余种写法。此外,山谷善于运用特殊的笔法语言,如用行书笔法写草书,将草书速度慢下来,别创理性一路草书;善于运用篆籀笔法,中锋用笔,力含其中,线条凝练,韧劲十足。
二是笔法呈现出“五美”的特点,即变化之美、对比之美、韵律之美、力量之美和个性之美。比如强调对比方面,有的甚至到了非常夸张的地步,给人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包括线条的粗细、长短、虚实,字形的大小,提按的轻重,速度的快慢,转折的方圆,墨色的浓淡和力量的强弱等。又如在个性之美方面,提倡“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勇于创新,敢于超越前贤。独创“高捉笔双钩法”“令腕随己意左右”等,掣笔有力,故其字骨力劲健。
三是笔法的内涵十分丰富,可归纳为三个“合一”,即临研创合一、诗禅书合一、人书道合一。强调读帖要“入神”“熟观”“会之于心”,才能懂得古人的笔法,“下笔时随人意”。融诗禅书为一体,诗风即书风,禅味即书味。其书法带有明显的禅味,线条干净,没有一丝尘埃气,有一种凛然的庄严感。善于以书明志,以书弘道,以书抒情。
李志强(中国铁路书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当代研究型书画家团队成员):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次何老师展出的两幅作品都是源自黄庭坚,一幅大字、一幅小字。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中看到他对黄庭坚内在文化性的一种理解。我们的理论研究要跟创作怎么结合起来,怎么将理论研究融入创作,应该说,何老师给我们做了表率。
刘德举(中国书协会员、中国当代研究型书画家团队成员):董其昌把用笔问题放在书法之首位,并提出了“提得笔起”的著名论断。他说:“发笔处便要提得笔起,不使其自偃,乃是千古不传语。”“提得笔起”是中锋用笔所需。毛笔的笔毛是柔软的,构造为圆锥形,其毛是一层一层卷起而成,当醮墨后,中间、锋尖含墨就多、就浓,边缘、副毫含墨就少、就淡,写字一般都用宣纸,其主要特性是化水性好,如写字用中锋,则笔画中间的墨色最浓最黑,两边边缘的墨色就淡、浅。这样的中间黑边缘淡的笔画,就显示了一种立体感之美。笔按下,笔锋就会变。为了在行笔中保持中锋不变,就须提笔调锋。在运笔写字过程中,是笔笔有提,笔笔有按,有提就有按,有按就有提。有提、有按、有节奏地运笔谓之“写”。这是“写”与“画”“刷”“涂”的区别所在。“提得笔起”是克服书法时弊之需。不少书家提不起笔,有的驻笔按锋时,不能及时提笔,则线条必然板滞臃肿;有的将行笔简单化、直白化,很多笔画感觉就像是用刷子刷出来的一样,毫无韵味可言。有的不会运笔,如董其昌所说:“作书须提得笔起,不可信笔。盖信笔则其波画皆无力。提得笔起,则一转一束处皆有主宰。转、束二字,书家妙诀也。今人只是笔作主,未尝运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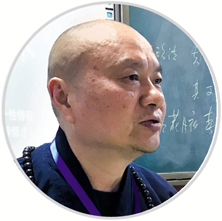
释悟才(浙江桐庐圆通禅寺住持、中国当代研究型书画家团队成员):洪亮先生在《书法原理讲稿》一书中说:“书法笔法的艺术表现是书者在书法笔法规律性和规定性基础上的艺术发挥,是因人因时而异的,它是因时空的变化和情绪情感的变化而变化的。”下面,我从八大山人所书《千字文》的个性特征,浅议一下技术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这件作品中有许多具有生命价值和生活艺术典型代表的字,它们既有生命的灵魂,又有身体的姿态;既能表达做人标准,又能表达哲学思想;既有壮志凌云的向上精神,又有有容乃大的豁达境界。这既是书法技术升华到书法艺术的具体表现,也是八大山人书《千字文》的无穷魅力之所在。从八大山人书《千字文》中可以看出,书法的笔法和字法所表现的艺术效果,并非是其刻意为之,因为艺术具有不可复制性。若八大山人创作下一篇《千字文》,同一个字也许成为另一个不同的艺术形象。其《千字文》的艺术表达,是随时空环境和心情心性的变化而变化的。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文字内容不会变,中锋行笔不会变,集诸家之长创作自己的风格不会变。总之,书法技术是书法艺术的基础,书法艺术是书法技术的升华。
李志强:悟才法师对八大山人书法的理解具有一定的个性,我们不一定会产生和他一样的想法,但是他的这种想象力会给我们带来很好的启示。八大山人的书法是非常高级的,他的线条宽窄度变化大、起收动作很小,看似简单的线条却有丰富的构成,线条的质量非常高。这使他消泯了很多尘世的念想,有一种提纯的东西,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

傅先锋(中国当代研究型书画家团队成员):我在这里浅谈一下智永《真书千字文》里的笔速问题。所谓“笔速”,即运笔的速度。它不只是书写快慢的问题,具体到智永《真书千字文》,如“辰”字,短横露锋起笔,由快渐慢回锋收笔。顺势撇出,节奏明显,至末笔捺画露锋起笔,渐按转至渐提收笔。影响笔速的主要因素有墨的浓淡、毛笔弹力的强弱、字体的大小、笔画本身的需要及纸张(如生宣、熟宣、半生不熟、牛皮纸、复印纸)等。墨浓则笔滞,迟滞的笔速反过来又影响了书写者的情绪与效果,孙过庭《书谱》也有“五乖五合”之说。熟能生巧,精到的用笔、恰当的笔速来源于长期的临帖与严格的训练。

张江莉(北京江悦文化有限公司创始人、中国当代研究型书画家团队成员):在临习王羲之《兰亭序》的过程中,我深切感悟到“牵丝映带”的用笔是行书书写的一大特点,也是体现秀美俊朗书风的重要笔法,其妙趣横生,变化很多,《兰亭序》就是其美感的顶峰体现。
“牵丝映带”的书写需要掌握很高的提按技巧,在开始下一笔之前笔尖抬高,但不能完全离开纸面,下一笔要笔尖轻落,稍后完成行笔及适时适度提按顿挫,即一笔完成这个牵丝书写,这时会在纸面上留下很细的行笔痕迹,这就是牵丝的纸面呈现。其运笔过程中需要注意:一、如果是落笔后在纸面上呈现出很粗的实线,那就是实连而不是牵丝了,这是牵丝与其他笔法的一种区别体现。二、如果笔尖离开纸面,在空中完成,书写过程中笔断意连,行笔气未断。整个书写过程字也是适时适度地提按顿挫动作贯穿,这个是笔断意连,而非牵丝笔法的呈现。
总而言之,牵丝用笔作为行书书写中独特的笔法,需要注意行笔中的提按顿挫,以及要把握配合书写中气息、节奏等。字字不同,则笔笔不同,上下气息笔意切不可断。映带则是这样产生出来的笔与笔、字与字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长期的训练过程,掌握了牵丝笔法的运用,就能书写出妙趣横生、变化多样、流畅自然、令人心旷神怡、回味无穷的行书作品。
免责申明:
免责申明:
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书法报网立场。

- 联系我们
- 咨询电话:027-65380795
- 书法报互联网(湖北)股份有限公司 网站简介
-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街水果湖横路7号4楼01室
- 关注我们
- 微信公众号:shufabao-net
- 邮箱:shufabaonet@163.com
- 中国书法第一融媒体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