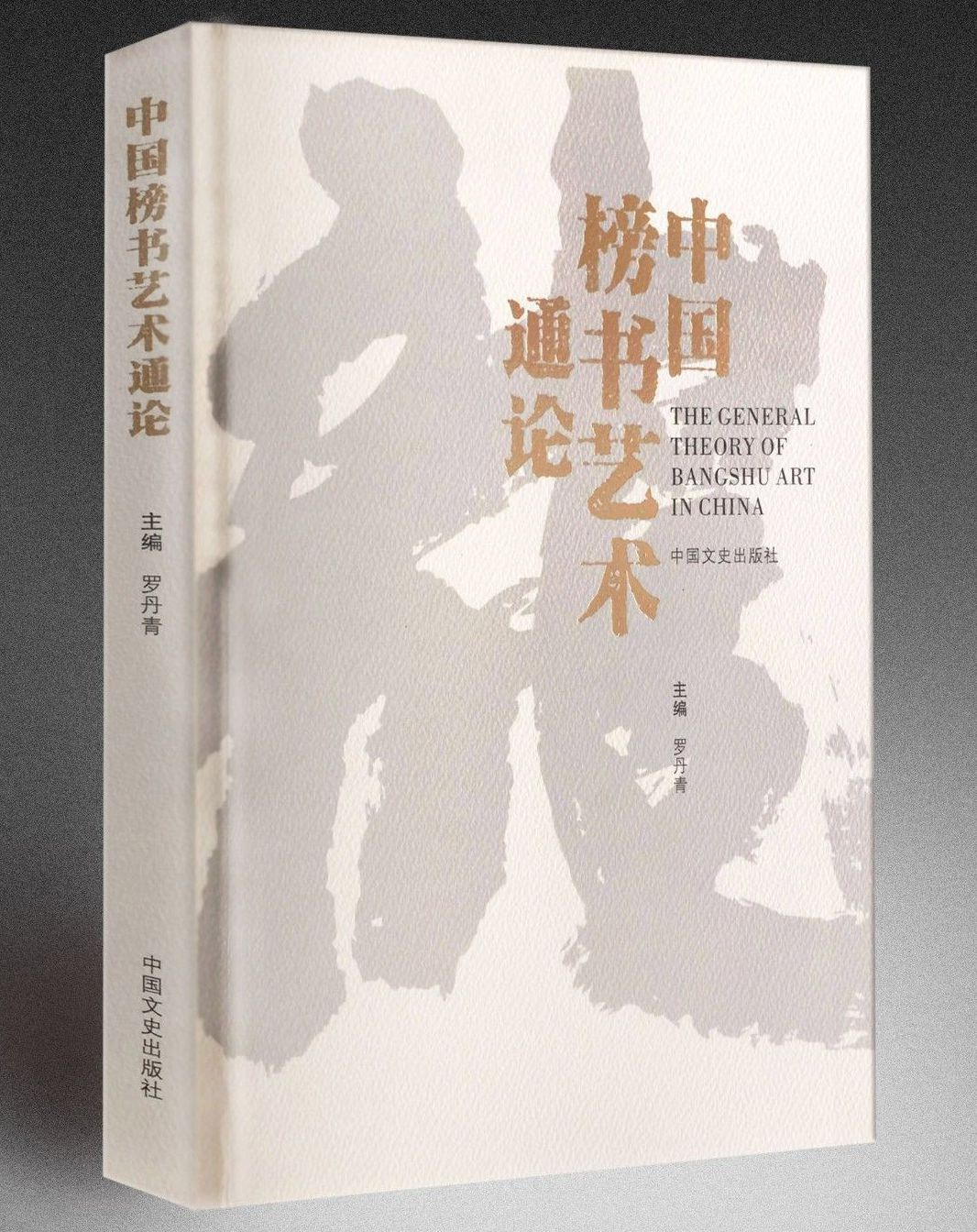0/500
翁同龢与骨董商的书法交易
2017/05/23 来源:书法报 责任编辑:李依默 作者名称:谭 帅;
翁同龢与骨董商的书法交易
——晚清官员书法交易的一个侧面
■谭 帅
流散于民间的法书遗迹经康、雍二朝收集,内府收藏规模已相当可观。乾隆更是以帝王之身份下力气搜集法书名绘、清玩骨董,当时河南宋权、宋荦父子宝藏的法书名画全部通过进献的方式归入内府;经乾隆下旨进行抄家,清初大鉴藏家梁清标庋藏的巨迹进入内库;其他如冯铨、高士奇、孙承泽、安岐等人所收藏的古代书迹一并被通过各种方式网罗进内府。至此,“清宫所积累的法书名画日盛一日,几乎民间流传的珍贵墨迹,大都归于内府收有了”(杨仁恺《国宝沉浮录》)。可惜好景不长,乾隆之后,清朝逐渐步入穷途末路之境,社会危机四伏,内府藏品大规模之流失则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咸丰一朝内忧外患,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加剧了社会动荡;英法联军入侵北京(1860年),将圆明园付之一炬,大量法书遗迹遭到野蛮的掠夺与毁坏。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再次进犯北京,藏于圆明园、乾清宫、养心殿的藏品遭到了致命的破坏,或被侵略者付之一炬,或被运往国外,或成为八国士兵的侵略胜利品。战乱之际,太监、侍女监守自盗,通过掉包、盗窃等方式,将内府所藏大量珍贵藏品带出宫外,数量多达数千件。不过,这倒为晚清官员进行收藏活动提供了条件,大量内府藏品流入琉璃厂商贾之手,晚清官员常结伴而行游厂进行收藏,客观上造就了琉璃厂书画交易的繁荣。
翁同龢的收藏活动主要以琉璃厂为中心。按《翁同龢日记》载,到厂购买是翁同龢收藏的主要方式之一。光绪二年(1876年),翁同龢饭后游厂,“购得董书长吉诗卷、王梦楼条(共十两)”。按当时的物价计算,购买一双狼皮暖鞋需京银1.4两。董其昌的诗卷与王文治的条幅加在一起才不过十两银子。光绪二十年(1894年),翁同龢在厂肆中见到了祝允明的行楷立轴,甚精,但价不昂;又花四两京银买到了刘墉的对联,真是如获至宝。按震钧在《天咫偶闻》中的记载,刘墉书作在当时的价格是很昂贵的:
厂肆之习,凡物之时愈近者直愈昂……书则最贵成邸(成亲王)及张天瓶(张照),一联三四十金。一帧逾百金,卷册屏条倍之。刘文清(刘墉)、王梦楼(王文治)少次。翁苏斋(翁方纲)、铁梅庵(铁保)又少次。陈玉方(陈希祖)、李春湖(李宗瀚)、何子贞(何绍基)又次。陈香泉(陈奕禧)、汪退谷(汪士[钅宏])、何义门(何焯)、姜西溟(姜宸英)贵于南而贱于北。宋之四家最昂,然亦仅倍成邸。松雪次之,思白正书次之,然亦不及成、张;行书则不及刘、王。若衡山、希哲、履吉、觉斯等诸自郐。此皆时下赏鉴,而贾人随之。
光绪二年,翁同龢曾在琉璃厂中见到金农临《华山碑》横幅与刘墉所书的《袁君墓志册》,但因价奇昂并没有购得。根据震钧的记载,虽然收藏家头脑中的“贵古贱今”的思想已逐渐淡去,但其时最贵的仍是宋四家的墨迹。光绪十七年(1891年),听说琉璃厂清秘阁新购买了一批原属于定亲王府的字画,翁同龢便赴厂观看。米芾的《珊瑚帖》《一年帖》《复官帖》三帖装为一册,竟然标价至京银一千二百两!如此之高的价格只能使翁同龢直呼“索直昂”,怏然不悦地回到了家中。不过,在游厂中翁同龢亦有因捡漏而喜舞狂欢的时刻,同治九年(1870年),翁同龢在隶古斋中得见唐人临摹《观音经》十一册、梁同书的长卷以及张照的《普门六经册》,极精。这次翁同龢并没有同掌柜过多地讲价,急忙以巨价得之。此后,翁同龢曾三次在《普门六经册》上用相同的韵律题诗,足见他对这册巨迹的喜爱与珍视。
传世的拓本则相对昂贵,动辄数百金。同治元年(1862年),翁同龢到厂肆尊古斋见到《醴泉铭》拓本,在与掌柜商量过后,同意让翁同龢带回家。让有意收藏的买家带回寓所慢慢考订是当时琉璃厂商贾惯用的伎俩,一来是他们坚信藏品的真实性,二来则更有易于以高价成交。当晚翁同龢灯下谛观《醴泉铭》,古厚可爱,夜分始卧:
又《醴泉铭》一册,姚姬传旧物,梁山舟跋推重殊甚,以为即谓之唐拓亦无不可,今藏南城曾氏,笙巢侍御所欲售去者也。鲁君云此是宋时复本,亦宋时拓,自言曾见宋拓《醴泉铭》七八册,皆浑厚飞动,有龙蟠虎卧之致,此拓虽圆劲,然是枣木板本。鲁君鉴家,其言当不谬。
鲁君即鲁燮光(1817—1910),字瑶仙,与翁同龢岳父汤氏为世家之交,精鉴碑版,收藏巨夥。曾为翁曾源诊治,当日碰巧与翁同龢同在尊古斋。两日后,翁同龢将《醴泉铭》还至尊古斋并有意购买,但掌柜开出的二百金的价格让他知难而退。事实上,厂肆商铺中的有些拓本并不像商贾鼓吹的那般完美无瑕。一年后,当翁同龢再度来到尊古斋观赏《醴泉铭》,他对此帖表示出了一定的怀疑,庆幸自己没有入手:“有南斋诸公题跋者是数本合成,佳者圆厚飞动,余多纤弱矣(‘推而弗有’,‘推’字缺;‘百姓为心’,‘姓’字缺;‘绝后承前’,‘承’作‘光’;末行‘欧’字作‘点’)。”同治四年(1865年),有一贾人带着《醴泉铭》来到翁同龢的家中,索价更是飙到了五百金。
当朝拓本的价格则相对便宜,也在翁同龢的承受范围之内。同治八年(1869年),翁同龢到德宝斋商铺发现了康熙中叶所拓的汉碑数种,德宝斋掌柜答应了翁同龢的要求,可以让他带回家观赏。三日后,翁同龢来到德宝斋,与掌柜议定帖价,以四十金完成了这笔交易。
尊古斋、德宝斋、博古斋、宝珍斋、松竹斋等店铺都是翁同龢常流连驻足的地方,久而久之,他与这些商铺的掌柜也慢慢建立了友谊。有些商铺的掌柜富有一定的学识,如嵩华阁帖铺的主人,“颇知收藏,能篆隶,不俗”;松竹斋掌柜张仰山则能隶书,知隶法。有些掌柜则邀请翁同龢为他们鉴定藏品:“德宝斋掌柜约余至松筠庵观桂相国所藏《华山碑》宋拓本,开册即知其伪,纸墨薰染,字如唐隶,诸跋皆伪,并覃溪、竹君两跋皆赝鼎也,一笑置之。”在翁同龢辨别的同时,他们的鉴赏能力也得到了提高,这无疑会提高他们搜访藏品的质量。不过,有些店铺的主人眼力欠佳,店中所展示的藏品多不精,如论古斋帖铺,翁同龢看后认为“价昂而货无出色者”。
翁同龢政务繁忙,虽有意于收藏,但要做到每件藏品都亲力亲为是不现实的,往往需要厂肆商铺的“上门送货”。这些商贾通常能把握翁同龢的喜好,他们常把藏品留给翁同龢仔细考订。咸丰十年(1860年),尊古斋送来《阁帖》残本两册,不过要价极高:“《阁帖》是赵味辛旧藏,题曰‘祖本阁帖’,细勘,与余斋修内史本无毫发异,索直三百金。”似乎尊古斋送来的藏品要价都比较昂贵,同治二年(1863年),尊古斋送来一卷唐人写经,书法清挺,但索价极昂,翁同龢犹豫不决,“拟还之”。论古斋送来的藏品也比较昂贵,使翁同龢难以接受,“日前论古斋贾人自南来,挟书画数十件,内石谷册十二开,袁重其霜哺四卷皆佳,刘完夫小卷亦佳,皆重价未可得”。相比之下,博古斋与德宝斋送来的藏品通常价格不贵,翁同龢也能接受。同治二年,博古斋送来唐人《法华经卷》三卷,“自十八至二十凡三卷,共十五纸三百三十行,字法遒紧,下开赵、董,有项子京印记,孙氏艳秋阁物也,索直不多,拟亟收之,真如窭人获至宝矣”。经过一番还价,以十二金得到此卷,商贾获利,翁同龢也认为此是妙迹,淘宝成功。同治五年(1866年),德宝斋持《麓山寺碑》拓片来,翁同龢仔细考订后,认定是乾隆年间的拓本,而且商贩的要价也非常低,“拟购之”。偶尔博古斋的要价也非常高:“祁公《大观帖》博古贾人持来,欲质一千四百金,谢以六百金,不愿而去(止留二刻)。”在博古商人持来兜售的三个月前,翁同龢曾在好友处借观过此本,并临摹过翁方纲的题跋,而后连续几日沉溺于此。要价如此之高,一是因为此本年代久远,传承有绪,是传世的巨迹;二是拓本之内有翁方纲等人的题跋,这些附在拓本内的题跋无疑增加了商贩定价的砝码;三则是博古商人在收购此帖时可能打探到了翁同龢曾对此帖爱不释手,竟然到了费时失事的地步。
除了厂肆商铺贾人的上门兜售外,晚清时期还有一批行走于大江南北的骨董商。他们通过多方打听来了解藏家收藏的喜好、住址,并以此为据兜售藏品。他们多有着精明的头脑与诡诈的手段,慢慢将买家引入到自己的圈套之中:
有持李北海《戒坛铭》来者,字如指顶,大约是明拓,后有金正希一跋,又张志古一跋,疑北海书太轻弱,继而卖者又以末页来,则覃谿先生八十二岁跋,称此帖墨香盈几,曩曾借临,而立碑年月不符(应在开元三年,帖称二年)。又碑叙括州刺史李邕书(北海作括州刺史在开元五年)。与《唐书》不合,故辨其伪,此帖又从伪刻传摹云云。还价十吊,不售。
翁同龢根据自己对李邕书风的判断有所怀疑时,这位贾人似乎并不了解翁同龢的鉴赏眼力,又将帖后翁方纲的题跋拿出,结果弄巧成拙,败下阵来。翁同龢对这位贾人也是比较包容的,甚至还“还价十吊”,调侃了他一番,贾人匆匆离去。
有些上门兜售的商贾竟然以伪作出示,企图瞒天过海。有清一代法帖作伪十分盛行,尤其以吴中地区最为出名,这些伪作大多在外部装潢上制作精美,常取旧锦装池,外加檀匣,以冒充传世旧拓。不过这些雕虫小技逃不过翁同龢的法眼:“有以《怀仁圣教序》来售者,装潢甚佳,帖乃伪作。”有些作伪的工匠技术精湛,不仅精于摹拓、翻刻,甚至达到了乱真的地步,再附上名家鉴藏印记与题跋保障伪作的“真实性”,有时翁同龢也辨别不出真伪:“有持《大观帖》来者,纸墨尚旧,有‘南薰殿宝’及张潜印、初顺园印、燕园考藏印,又有珊瑚阁藏及云间王鸿绪藏记,恐未的,总之,是翻版耳,第一第二卷无‘裹’‘鲊’,‘鹘’不清,两帖第三卷‘亮’字磨去,无痕可寻。”
值得注意的是,晚清时期仍有书画船的存在。光绪三年(1877年),翁同龢请假回籍,在老家常熟闲适的生活中,翁同龢依然保持较高的收藏热情,在前往书画船购买藏品的同时,亦能通过书画船主人见到当地的骨董商:
晨再入城买零星物,再至千顷堂买书一两种,再至书画船购石谷小帧、麓台矮幅,皆精(四十四元)。书画船主人武(月舟)邀余同诣张子祥(熊,平湖人,贩古董,能画,七十余矣)家看沈石田长卷(文衡山补成,虞山王虞卿所收,有邓黻长跋,孙慈峰收藏印,长六丈)、石谷《江乡渔乐图》(长二丈),皆妙,烟客册八页,尚可,归已午正矣。
在翁同龢的日记中,我们经常能发现他与骨董商议价的记载,“需要指出的是,晚清文物商所开之价(即索价)往往会和实际成交价差别很大,成交价低于开价的三分之一、一半、甚至一半以上是经常的事”(白谦慎《晚清文物市场与官员收藏活动管窥:以吴大澂及其友人为中心》)。翁同龢善于同商贾打交道,顺利地讲价节省了不少财赀。同治八年(1869年),有一位贾人向翁同龢兜售《百石卒史碑》拓片,在确认为元拓无疑后,询问价格,三百金的价格让他一笑还之,并没有当即还价。一个月之后,不知通过什么办法,翁同龢最终以二十六金的价格收入囊中,这仅是索价的十分之一!类似的事件也曾在翁同龢开缺回籍时发生,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一位名叫毕藻卿的商贾携明拓《孔彪碑》来到虞山西麓下的瓶庐居,开口便索价五十元;两日后翁同龢以二十九元的价格购得此物。又同治十二年(1873年),翁同龢在上海城中的醉六堂书坊见到了明拓《皇甫君碑》与《道因法师碑》,议价时没有掌握好分寸,竟把书坊主人惹怒,“主人怒而逐客”,翁同龢也只好识趣离去,去找老友即时任上海道台的沈秉成诉说这次尴尬的经历。

免责申明:
免责申明:
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书法报网立场。

- 联系我们
- 咨询电话:027-65380795
- 书法报互联网(湖北)股份有限公司 网站简介
-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街水果湖横路7号4楼01室
- 关注我们
- 微信公众号:shufabao-net
- 邮箱:shufabaonet@163.com
- 中国书法第一融媒体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