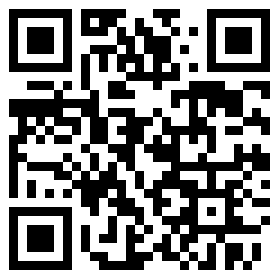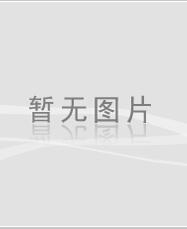0/500
“尚法”与“达性”:唐代书法审美的对立与中和
2017/05/12 来源:书法报 责任编辑:李依默 作者名称:朱化杰;
“尚法”与“达性”:唐代书法审美的对立与中和
■朱化杰
“尚法”与“达性”是唐代书法的两种审美取向。从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等人的书法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他们对前贤的广泛取法,以及自我作法的意识。但是同时,我们在张旭、怀素、孙过庭等人的书迹中看到的却是情感的自由抒发和笔墨的淋漓尽致。检索唐代的书法理论文章,不难发现,唐人对书法“达性”的审美更为偏好。而“尚法”作为“达性”的基础和先决条件也被时人所广泛论证,两者是由对立到中和的过程。
提及唐代书法的整体特征,今人习惯于用“唐尚法”这个概念来概括,这种说法散见于各种著述中。而“唐尚法”这个概念的提出,可以追述到董其昌。他在《容台集·论书》中说道:
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或曰:“意不胜于法乎?”不然。宋人自以其意为书耳,非能有古人之意也。然赵子昂则矫宋之弊,虽己意亦不用矣。此必宋人所诃,盖为法所转也。
其在《画禅室随笔》中又说:
晋宋人但以风流胜,不以无法,而妙不在法。至唐人始专以法为蹊径而尽态极妍也。
董其昌在这里将晋、唐、宋的书法风格概括为“韵”“法”“意”,是试图站在一定高度上抓住每个朝代的主线。他在此处所讲的“法”,便是站在整个唐代文学艺术发展的角度得出的结论,即唐人崇尚将两晋六朝的风格法则化。钱泳在《履园丛话·书学》中提到:
有唐一代,崇尚法书,观其结体用笔,亦承六朝旧习,非率更、永兴辈自为创格也。
清初冯班承继董其昌的观点,在《钝吟书要》中指出:
结字,晋人用理,唐人用法,宋人用意。用理则从心所欲不逾矩。因晋人之理而立法,法定则字有常格,不及晋人矣。
晋人尽理,唐人尽法,宋人多用新意,自以为过唐人,实不及也。
冯班反复强调“唐人用法”,但何谓“法”,他解释说“意即是法”。关于“意”,冯氏曾指出用功学习古人,学习本领便是“意”,“书至成时,神奇变化,出没无穷。本领精熟,则心意自能变化”。由此可见,冯班虽然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论书体系,但是在“唐尚法”这个问题上,还是同董其昌基本一致的,即效法前人的书迹。
至清乾隆年间,梁巘在《评书帖》中分别用一个字来概括各时期的书法风貌,他写道:“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梁氏《评书帖》篇幅短小,段与段不相连属,因此不能得出他所言的“法”的真正内涵。但是从董其昌和冯班的观点来看,此处所言的“法”,指学习、效法古人的可能性较大。不管其真实情况如何,从此以后,“唐尚法”这个概念却被广泛征引。
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唐尚法”这个概念被征引的时候,已经偏离董其昌、冯班等人的本来意思,被解读为唐代书法崇尚自身的法度谨严,而偏离其崇尚学习前朝书法的轨道。究其原因,就在“法”字上。关于书法中的“法”,可以追溯到东汉崔瑗《草书势》中的“法象”这一概念。“观其法象,俯仰有仪。方不中矩,圆不副规”,崔瑗在这里所说的“法象”指的是书法与自然的关系,即书法艺术来源于自然万象,并能够借以表现自然万象的美,单就“法”来讲,是“师法”的意思。至南朝齐时期,“法”的内涵还是延续了这一传统。唐张彦远《法书要录》中所录《南齐王僧虔论书》中有诸多关于“法”的材料:
王平南廙是右军叔,自过江东,右军之前,惟廙为最,画为晋明帝师,书为右军法。
晋齐王攸书,京洛以为楷法。
亡高祖丞相导,亦甚有楷法,以师钟、卫。
如此种种,不胜枚举。由此可以看出,在南朝齐时期,“法”还是师法、取法的意思。但到梁时,“法”的内涵发生了变化。这一点可以从虞龢《论书表》中窥见端倪:
桓玄爱重书法,每宴集,辄出法书示宾客。
又如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
《乐毅论》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轻言,今旨以为非真,窃自信颇涉有悟……此书虽不在法例,而致用理均。
又如庾元威《论书》:
所学草书,宜以张融、王僧虔为则,体用得法,意气有余。今六人之法虽存,十五之篇亡矣。
由此可见,虽然从南齐到南梁,中间仅相隔了不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法”这一概念的内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师法”发展为“法则”。
到了唐代,“法”的概念延续南北朝后期的内涵,多指“法则”。检索唐代书论,我们可以发现,唐代对于“法”的重视。如《法书要录》中崔备《壁书飞白萧字记》所述:
加以子云与国同姓,所书“萧”字,圜卷侧掠,体法备焉。
其后张敬礼、王逸少、子敬并称绝妙。子云曲尽其法。
这些材料中的“法”的内涵都是“法则”的意思。唐代其他文献材料,也能够佐证这一观点。如李嗣真《书品后》中有“此法更不可教人”之言,徐浩《论书》中有“程邈变隶体,邯郸传楷法”之言,等等。
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法”的概念在唐代即是“法则”的内涵,那是否与上文所论述的梁巘等曲解董其昌、冯班等人的观点相左呢?其实不然。“法”在唐代指“法则”的前提是文句论述学习古人书法。除了上述所引材料能够看出这一点以外,还有如张怀瓘《书仪》:
今穷伪略之理,极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且法既不定,事贵变通。然古法亦局而执,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
从上述材料可知,“法”这一概念在经历了最初的“师法”这一内涵以后,在南朝时期开始以“法则”的内涵来使用。但是,此时的“法”在使用时也有其特殊的语境,即大多在论述学习前人书法时使用。由此可见,探讨“法”这一概念还应把目光重点放在“师法”的范畴内进行。
但是有一种现象,唐代人在“师法”的基础上,也开始“自我作古”,其自身内部也形成了许多法则。因此,“法”的内涵在唐代进一步扩大了,其中既包括对前朝约定俗成的法则的遵守,也开始在自身范围内进行规范,形成自己的法则。后者经常被征引“唐尚法”的研究者所关注,而前者却常常被忽视。
解决了“法”这一概念在唐代的内涵,我们就会将这一结论推及唐代书家身上去印证。无论是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还是颜真卿,都能够相合。但是怀素的草书、张旭的狂草、颜真卿的行书却处在对立面。例如,张旭的狂草是连绵恣肆的,但不能够说是遵守法度的。其实,检索唐代的书法理论文献,就会发现,这种与“尚法”对立的“抒情”性,是在唐代就被广泛探讨的,而关于“尚法”与“抒情”的调和,也是许多唐代书家所探讨的问题。
孙过庭在《书谱》中就深入探讨了“表情”这一书法艺术的本质。他说:
然后凛之以风神,温之以妍润;鼓之以枯劲,和之以闲雅。故可达其情性,形其哀乐。验燥湿之殊节,千古依然;体老壮之异时,百龄俄顷。
孙过庭认为,要以“凛”“温”“鼓”“和”等手段,达到“风神”“妍润”“枯劲”“闲雅”的艺术境界,并说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书法“达其情性,形其哀乐”的价值追求。
而针对唐代书家所广泛取法的二王书法,孙过庭也高屋建瓴地提出二王书法的要旨是“传情”:
但右军之书,代多称习,良可据为宗匠,取立指归。岂惟会古通今,亦乃情深调合。
孙过庭把唐人奉为圭臬的二王书法,尤其是王羲之书法的最高价值定义在“情性”上,是对晋以来书法自觉意识的延伸。可以说,对于书法表情达意功用的探讨,自始至终就没有停止,其中出现许多偏颇。但是,孙过庭强调“情性”并没有忽视技法在书法上的作用。他在《书谱》中指出:“夫运用之方,虽由己出,规模所设,信属目前,差之一毫,失之千里,苟知其术,适可兼通。心不厌精,手不忘熟。”对于点画的要求,孙过庭是很苛刻的。而每一种点画形态、位置、干枯等,孙氏都作了探讨:
至若数画并施,其形各异;众点齐列,为体互乖。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违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常迟,遣不恒疾;带燥方润,将浓遂枯;泯规矩于方圆,遁钩绳之曲直。
孙过庭强调书法的艺术形态必须合古人之法,同时又要注重变化。有变化才能够丰富多彩,但是一味求变化则会有违协调。
此外,张怀瓘与孙过庭持相似观点。他在《六体书论》中说:“如人面不同,性分各异,书道虽一,各有所便。顺其情则业成,违其衷则功弃,岂得成大名者哉!”强调书法要顺从自己的性情。他在《书断》中又说:
夫古今人民,状貌各异,此皆自然妙有,万物莫比,为书之不同,可庶几也。
在张怀瓘看来,只有那些具有独特风格的书作才能称之为真正的艺术创作。正如人有不同的面貌一样,书法创作也应该具有不同于他人的风格面貌。同样,张怀瓘也是站在辩证的立场上来论述书法创作。他在强调书法要具有不同于他人的个性的同时,也不忘取法在书法学习和创作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他在《六体书论》中说:“学必有法,成则无体,欲探其奥,先识其门。有知其门不知其奥,未有不得其法而得其能者。”又说:
故学真者不可不兼钟,学草者不可不兼张,此皆书之骨也。如不参二家之法,欲求于妙,不亦难乎!若有能越诸家之法度,草隶之规模,独照灵襟,超然物表,学乎造化,创开规矩,不然不可不兼于钟、张也。盖无独断之明,则可询于众议;舍短从长,固鲜有败书,亦探诸家之美,况不理其祖先乎!
在张氏看来,要想得到书法的奥妙和要旨,就要找到学习书法的门径,而这一门径就是学习古人。如果不从学习古人的门径来学习书法,就是徒劳的。正如学习楷书不可以不学习钟繇,学习草书不可以不学习张芝一样。但是张氏强调,学习书法的门径并不是唯一的,要根据实际情况去选择,并最终到达无法的境界。正如他在《评书药石论》中所说:
圣人不碍滞于物,万法不定,殊途同归,神智无方而妙有,用得其法而不著,至于无法,可谓得矣。何必钟、王、张、索,而是规模?道本自然,谁其约限!
大文学家韩愈也认为,书法创作应该重在表现创作者自身的情感,随着自身情感的变化,书法所表现出的风格也应当是不断变化的。他在《送高闲上人序》中论及张旭草书时说:
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
他把张旭在草书创作中所传达的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等情感放在草书创作的第一位,把书法的表情达性功用作为草书创作的重要意义。认为草书之于张旭,便完全是情感宣泄的工具,而草书只是他情感的外化。
由以上书论文章可知,唐代对于书法表情达性的功用有辩证而深刻的认知。书法创作在经历了魏晋,尤其是东晋的艺术自觉后,在唐代迎来了新的高峰。文字的书写已经不单单起到记录的作用,而是更多地被赋予创作者微妙的情感,这种情感的变化体现在书法上,就是唐代行草书创作所呈现出的多姿多彩的面貌。
其实,初唐时期“尚法”和“达性”这两种审美观就已经出现并峙,并随后走向中和的道路。正如孙过庭与张怀瓘所言,书法创作不能仅停留在师法古人的层面,更重要的也是区别于前人的关键在于抒发自身独特的情感体验。唐代书家在全面师法古人的同时,也或多或少地加入了自己的认知,并自我立法,最终形成了一直影响到今天的成绩。而唐代的行草书家则在前人的基础上,大胆变革,在书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免责申明:
免责申明:
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书法报网立场。

- 联系我们
- 咨询电话:027-65380795
- 书法报互联网(湖北)股份有限公司 网站简介
-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街水果湖横路7号4楼01室
- 关注我们
- 微信公众号:shufabao-net
- 邮箱:shufabaonet@163.com
- 中国书法第一融媒体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