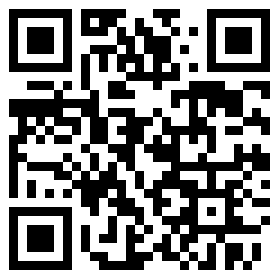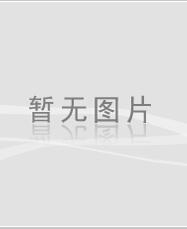0/500
二王名下四件楷书真伪浅述
2017/03/02 来源:书法报 责任编辑:李依默 作者名称:徐学毅;
二王名下四件楷书真伪浅述
■徐学毅
二王父子均无真迹存世,而摹本、刻本也往往存在或多或少的争议,本文拟对二王名下四件楷书的真伪作些浅考和简述。
一、(传)王羲之《佛遗教经》
末署“永和十二年六月旦日山阴王羲之书”,宋以前不见著录,赵明诚《金石录》云:“国初时人盛传为王右军书,惟欧阳公识其非是。”是知北宋欧阳修曾作辨伪,其《集古录跋尾》卷十“遗教经”条云:
右《遗教经》,相传云羲之书,伪也。盖唐世写经手所书。唐时佛书今在者,大抵书体皆类此,第其精粗不同尔。近有得唐人所书经,题其一云薛稷,一云僧行敦书者,皆与二人所书不类,而与此颇同,即知写经手所书也。
但苏东坡则委婉地反驳了这一观点:“以其言观之,信若不妄。然自逸少在时,小儿乱真,自不解辨,况数百年后传刻之余,而欲必其真伪,难矣。”黄庭坚则支持将此作定为赝品,既同意是“经生书”,又指出经文译出时羲之已经离世,还举出非常有力的证据。其《姚诚老所书〈遗教经〉后》云:
姚诚老书《佛垂般涅槃略说教戒经》(即《遗教经》)用笔有意态,惜乎不能耆老毕其能事也。世有贞观中敕书班行,经生书小楷一本,最端谨娴丽,世因谓之王右军书,盖不知弘始四年译此经,右军没已数年矣。
《遗教经》由姚秦鸠摩罗什翻译汉文后广为流传,而永和十二年秦鸠摩罗什年仅13岁,罗什来长安从事译经也是弘始三年(401年)十二月后,时右军已卒。当然罗什以前是否有此汉文佛经流传,文献并无记载。路远先生曾将唐刻残版《佛遗教经》与《中华大藏经》本比勘发现有十八处文字差异,但基本只是某单字使用不一,整句和较长词汇极少有出入,因此基本可判断出于同一翻译家,或许抄写过程辗转积累了讹误而已。另传有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楷书拓本,末署“永和十年四月十八日王羲之”,作伪手法如出一辙。
北宋董逌(yōu)亦云此作为伪作,但指出唐德宗时比丘道秀所写的《佛戒经》“与此经一体”,故可视其主张是道秀而非经生书,其《广川书跋》“遗教经”条云:
欧阳永叔以此为唐写经手,黄鲁直谓此书在楷法中小不及《乐毅论》……后人不见逸少迹,若碑刻所传,已多假伪,则临拓善工,自足惑世矣。尝得《佛戒经》,其碑乃比丘道秀书,与此经一体,率化众缘,共崇镌刻,则知为道秀所书,但世不传尔。道秀,德宗时人,其书当建中三年壬戌,盖永叔、鲁直不见碑阴,故所评如此。
清钟德祥并不否定书风,而疑为后人集字。袁昶《毗邪台山散人日记》载钟德祥所说:
《遗教经》出于姚秦,王右军所书。疑为后人集右军书为之,如《圣教序》例。
褚遂良《右军书目》仅录右军真书四十帖,张怀瓘《二王等书录》载:“今天府所有真书不满十纸。”《书估》载:“如大王草书字直一百,五字乃敌一行行书,三行行书敌一行真正。”可知唐时右军真书已相当稀少,后人要摹其楷书集成两千余字的《遗教经》既费时力也不易实现,怀仁集《圣教序》、大雅集《兴福寺碑》均摹行书即是例证。另帖末署“王羲之”与当时普遍无名款的风气不合。
综上,将《遗教经》定为赝品庶几不谬,需继续探讨的只是经生道秀书。道秀书面目今已不得而知,而二王伪作宋人多疑出于唐经生,如黄庭坚《题〈东方朔画赞〉后》云:“如佛顶石刻,止是经生书。”《广川书跋》说右军《告誓文》真迹于岐王宅被焚后其晚出的碑字“似是唐经手拓摹以传”。米芾《海岳名言》云:“唐官诰在世为褚、陆、徐峤之体,殊有不俗者。开元以来,缘明皇字体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时君所好,经生字亦自肥。开元以前古气,无复有矣。”若果是经生,以书迹判或写于开元前。
二、(传)王羲之《曹娥碑》
此作自宋即聚讼纷纭,今人启功、杨仁恺、黄文宽、梁少膺和中田勇次郎等均有相关考述,对其书于何时见解不一,但均定为非右军书。笔者认为宜将绢本墨迹与拓本区别开来。
先说绢本。其文讹误频见,如“千夫失声”作“千大失声”、“何怅华落”作“何长华落”,文意不通,自非文士名流所写。又柳宗直与韩愈题跋、僧权与怀充签署乃同一笔迹,题记有“丁末”误作“巳末”等都是伪作证据。
再说拓本,万君超先生归纳为今存三种类型:越州石氏本、《群玉堂帖》和南宋刻本。南宋刻本源于石氏本或《群玉堂帖》,而《群玉堂帖》乃韩侂胄(tuō zhòu)据绢本摹刻,保留了唐人观款,既然绢本伪,则《群玉堂帖》与部分以《群玉堂帖》为底本的南宋刻本均伪,剩下探讨的只有石氏本。
民国《新昌县志》称南宋初石邦哲摹刻《越州石氏帖》中的《曹娥碑》为晋贤书,而此本无唐人题跋,前部分比绢本多出“怀充”二字,书风与绢本的笔力怯弱亦差距甚大,若称为右军书相对来说疑点少得多,但也有四点问题:一、为何降至北宋黄伯思《东观余论》才首次提及“逸少《曹娥帖》”与载有“跋逸少《升平帖》后”;二、“在洽之阳”误作“社洽之阳”、“千夫失声”误作“千夫共声”;三、末存“三百年后碑冢当堕江中,当堕不堕逢王叵”,清末民国欧阳辅《集古求真》云:“此等不经之言,与《保母砖》如同一辙,何右军父子均书其怪异有如方士妖僧乎?蔡雍之‘雍’字亦古所未有。”四、“蔡邕”作“蔡雍”。
针对以上四点,笔者觉得尚不能判定非右军书。杨仁恺先生《晋人〈曹娥碑〉墨迹泛考》文中说倪云林题石本《黄庭经》提到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表》载有《曹娥碑》等真迹,但检阅范祥雍点校的《法书要录》并无记载,或许倪云林有误,且著录也只能作为辅助而非有力证据。“在”“失”两字误刻,可能与“社”“共”形近,并不意味底本伪。文末有谶记也并非就是“方士妖僧”伪作,虽然献之《保母砖》末记“后八百余载,知献之保母宫于兹土者,尚可考焉”,与距离出土时间竟大体契合,显系后人伪托,但问题是作伪者为何会采用如此愚蠢、画蛇添足的手法?而姜夔、周密、赵孟頫等题跋又俱不责此妄言?我觉得必因唐宋元人见古人书亦时有谶记方能解释,宋陈思《书苑菁华》卷一有类似记载:“斯(李斯)《秦望纪功石》云:‘吾死后九百四十年间,当有一人代吾迹。’”同书录虞世南《劝学篇》云:“羲之于山阴写《黄庭经》,感三台神降;其子献之于会稽见一异人,披云而下,左手持纸,右手持笔,以遗献之。”即使以上文献或不可靠,但《书谱》也曾批评过献之“假托神仙”,则知唐以前诸多荒诞不经的传闻流行甚广,而生活于盛行撰写《搜神记》此类志怪年代的王羲之,又在并非“书与某人”的情况下顺手记一两句谶语怪闻并非绝无可能,起码不能因此便斥之伪赝。另外“邕”字作“雍”,杨仁恺先生已有考释,结论是汉晋之际“邕、雍实本一字”,并非为避讳北周宇文邕。可见,绢本《曹娥碑》基本可定为赝品,但对越州石氏本尚未能完全定夺。
三、(传)王献之《乞假帖》
《乞假帖》刻于《宝晋斋法帖》,黄伯思《东观余论》曾语《乞假表》是“大令传于世佳者”,田熹晶认为:
此《乞假表》当与《乞假帖》为同一书迹。因为《乞假帖》是写给皇帝,请求准假的书帖,所以书写极为恭谨,与献之其他楷书字帖极为接近,故黄伯思认为是小王真迹,为“暮年遒美之时”所书。
田先生所考是太元十年(385年)王献之从吴兴太守被擢为中书令时所写,所言时间、事件均似合理,文辞上似可信。刘茂辰等先生《王羲之王献之全集笺证》以帖语“违远坟墓,奄冉五载”,又羲之卒于升平五年(361年)而推算写于太和元年(366年),似乏说服力,因为此年献之才23岁,不可能居于异地已然五载,何况丁忧也需三年。此帖“圣”字另起一行,《绛帖》刻羲之书与皇帝的楷书《霜寒帖》“圣”字亦另起一行,《姨母帖》墨迹“姨”字也另起一行,都与《乞假帖》同。又《乞假帖》字距行距均显宽绰,与楷书偏多的《廿九日帖》摹本也类似。从文句和格式上看,此帖似无明显破绽,只是为何宋以前没资料语及此帖?其部分文字的书风与献之可靠书札中的楷书虽有个别接近处,但总体行气不畅,缺少大令典型的沉厚跌宕,是否为摹刻不精所致呢?又或是王献之当时书写过于“恭谨”的态度所致?虞龢《论书表》载:“子敬常笺与简文十许纸,题最后云:‘民此书甚合,愿存之。’”说明献之向帝皇上疏确曾怀着刻意为佳的心态。
四、(传)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
本人曾发表文章探讨它未必为王献之书,其中提到陶弘景说右军《洛神赋》诸书十余种“当是零落,已不复存”,而柳公权鉴定未必可靠,宋邵博、董逌疑其伪,此处再补充几则材料。
黄庭坚亦疑其伪,其《题唐本〈兰亭〉》云:“《洛神赋》余尝疑非王令遗墨,岂古本既零落,后人附托之耶?周越少收敛笔势,亦可及此。”又《题〈洛神赋〉后》云:“余尝疑《洛神赋》非子敬书,然以字学笔力去之甚远,不敢立此论。及今观之,宋宣献公(宋绶)、周膳部(周越)少加笔力,亦可及此。”黄伯思《东观余论》云:“此赋草书世传王大令书,然结体殊不类献之,而颇似智永,疑其遗迹也。至《洛神》小楷,则子敬书无疑矣。世以小王好书此赋,故凡有《洛神》书本皆归之子敬。”虽然黄氏认为《洛神》小楷为子敬书,但其“世以小王好书此赋,故凡有《洛神》书本皆归之子敬”的观点却又道出“古本既零落”的情况下,凡传为子敬《洛神》均不排除“后人附托”的可能。
唐李嗣真《后书品》曾说自家藏有钟会正书《洛神赋》。清徐树丕《识小录》载李嗣真论右军书格不同云:“《曹娥碑》其容憔悴……《画像赞》《洛神赋》姿仪雅丽,有美女插花之象。”清王士祯《居易录》载有褚遂良《临子敬〈洛神赋〉》。清姚衡《寒秀草堂笔记》有版本方面的疑问:
二王并书《洛神赋》。右军者,世不经见;大令所书,《宣和书谱》所收已非完本。《汝帖》刻于大观时,亦止“嬉”字五行。快雪堂所刻肥本,有“世南”半印,唐初已仅仅存此。宋高宗绍兴年间,竭力搜索,止得九行。贾秋壑复得四行,属其客廖莹中刻之于玉,世所传《玉版十三行》是也。赵松雪跋谓“悦生”葫芦印及“长”字印,此并无之,尾有“宣和”二篆书,与赵本又不同。
唐韦述《叙书录》云“小王行书《白骑遂》”,黄伯思、王澍称《淳化阁帖》中行楷体《白骑遂帖》为献之临书,此札与《廿九日帖》书风相近,十三行与此两帖比较均有差异。
五、小结
王僧虔与虞龢均提到张翼效右军《自书表》,让羲之感慨“小子欲乱真”,陶弘景说右军辞官后“略不复自书,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别也”(清梁章钜《浪迹丛谈》载纪文达认为代笔人是任靖),并提到当时存在不少仿作和摹本:
臣涛言一纸,此书不恶,不识谁人迹,而非右军父子,又似是摹……后又治廉沥狸骨方一纸,是子敬书,亦似摹迹……前黄初三年一纸,是后人学右军……五月十一日纸,是摹王珉书,被油,尚想黄绮一纸、遂结滞一纸,凡二篇,并后人所学……
张怀瓘《二王等书录》云:
且如张翼及僧惠式效右军,时人不能辨,近是以有释智永临写帖,几欲乱真,至如宋朝多学大令,其康昕、王僧虔、薄绍之、羊欣等,亦欲混其臭味,是以二王书中,多有伪迹。
右军当时已有代笔和能乱真迹者,后世又有许多“锐意摹学”“使类久书”者,梁距东晋不远而仿作和摹本盛行程度业已如此。《广川书跋》提到陶弘景已鉴《狸骨帖》“是子敬书,亦似摹迹”,至宋代却又定为右军书;陶弘景《论书启》评“尚想黄绮一纸”为“后人所学,甚拙恶”,而《法书要录》则又载为右军正书且广为流传,如大英图书馆S.3287号唐代学童平日临写练字的敦煌卷子中即有《尚想黄绮帖》,这一现象也值得注意。
免责申明:
免责申明:
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书法报网立场。

- 联系我们
- 咨询电话:027-65380795
- 书法报互联网(湖北)股份有限公司 网站简介
-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街水果湖横路7号4楼01室
- 关注我们
- 微信公众号:shufabao-net
- 邮箱:shufabaonet@163.com
- 中国书法第一融媒体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