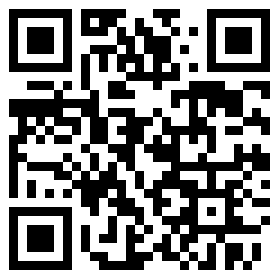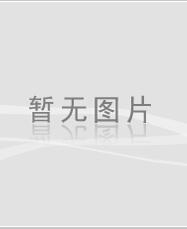0/500
怀素“以狂继颠”草书精神初探
2017/04/20 来源:书法报 责任编辑:李依默 作者名称:张社教;
怀素“以狂继颠”草书精神初探
■张社教
论及中国书法,草书的艺术影响力不可忽略。唐代是草书艺术的高峰,这座高峰中的“双子星座”张旭、怀素则是无法绕过的峰岳。为什么怀素这个僧人草书家能够屹立书坛千余年?其实只有一个答案——怀素个人在草书方面的创造性。所谓晋尚韵、唐尚法,且唐人将法度推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怀素身处这个时代,能够冲破世俗桎梏独与天地对话,的确是那个时代的“超人”!当时王羲之受到唐太宗的追捧,时人趋之若鹜,怀素并不在意当代的艺术潮流。他能借题发挥,更多地在“一笔书”的领域探索。青少年时期的书法,凭借的是艺术直觉。李白认为“张颠老死不足数,我师此义不师古”。怀素草书的确和魏晋草书不同,由于少年怀素缺少师承“不师古”,也不左顾右盼看别人怎么看、怎么做、怎么说。可能正是他那时在师承方面的空缺,令他在书法上少了一份束缚,再加上他天马行空、我行我素的庄子精神,为他后来在书法创新上提供了沃土。
综合来看,怀素的成功得益于唐代这个文化和政治昌明的时代,个人独特的成长经历,以及师友的襄助和提携等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虽说“怀素家长沙,幼而事佛”,但从他生活的环境及早期的书法风格中,很少表现出佛门的禅意,更多地是不自觉地表现出了许多散淡自然,释怀“重生”,无束“乐生”,“天人合一”的庄子风骨。日本佛学家铃木大拙博士分析得非常清楚,他说:“禅师的最明显的特质是在于强调内心的自证。这种自证,和庄子的‘坐忘’‘心斋’和‘朝彻’是如出一辙的。”也可以说,怀素的经“禅”是对魏晋道学的延续,怀素是一腔道家情怀。
从整个时代因素来看,儒、佛、道三教互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罗香林《唐代三教讲论考》一文,通过对唐代三教讲论的具体考察,指出三教归一之旨,在唐代“久已普遍朝野”。陈寅恪说,“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如国家有庆典,则召三教之学士,讲论于殿庭”。三教讲论导致了学者以释道义理解释儒家经义,从而促进了儒家思想的转变。儒道合流,在怀素身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怀素的成长与家族环境也是分不开的。《自叙帖》中记:“颇好笔翰,然恨未能远睹前人之奇迹,所见甚浅。遂担笈杖锡,西游上国,谒见当代名公。”怀素早在7岁(一说10岁)时“忽发出家之意”,所谓“猛利之性,二亲难阻”,竟执意出了家。笔者翻阅大量史料,试图寻找一个不满十岁孩子执意出家为僧的答案,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合理、确切的说法。在1200多年前,中国处在农耕文化时期,在这个年龄段怎么可能看破红尘?那么,怀素出家为僧的动力是什么呢?《高僧传》记载,怀素算是书香门第,其曾祖父钱岳曾在高宗时做过纬州曲沃县令,祖父钱徽曾任延州广武县令,父亲钱强做过左卫长史,怀素叔父钱起为大历十才子之一。值得一提的是,他有个伯祖父释惠融,是个僧人,书法甚是了得。陆羽《僧怀素传》中说:“怀素伯祖,惠融禅师也,先时学欧阳询书,世莫能辨。”怀素的表兄邬彤也是唐代有名的大书法家。怀素幼时已是家道中落,在那种小农经济社会里,家里人都在为生计忙碌,小怀素根本没有环境和时间整天去习字。由此看来,怀素视书法如生命,不顾父母再三阻拦,执意出家,可能一是受到了家风的熏陶,二是受到了大书法家表兄邬彤的熏染。第三点,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更现实的可能是受伯祖父惠融禅师的影响。他压根就不是真心去做小和尚的,只是想借僧家的寺院作为栖身、糊口和习字处所罢了。要知道,唐代僧人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但怀素不受陈规戒律限制,性格和情怀一如既往地保留下来了。
怀素是幸运的,不仅有浓郁的家学氛围,更主要的是在社会交往中接触到诸多良师益友。这当中,首先要提及的就是张旭。张旭为人洒脱不羁,豁达大度,卓尔不群,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且与李白、贺知章相友善,杜甫将张旭、李白、贺知章列入“饮中八仙”,张旭工诗,又与贺知章、张若虚、包融合称“吴中四士”。要知道,张旭“微官薄禄,生活恬淡”,骨子里是一个深藏的道家(李颀诗说他“右手持丹经”),所以草书始终充满一种逍遥游的精神。张旭也是狂怪至极,以发蘸墨而作,如入无人之境,境随心生,没有束缚,没有顾虑。张旭说:“先贤草律我草狂,风云阵发愁钟王。”其弟子颜真卿没有张旭超脱,不敢“脱帽露顶王公前”。虽然笔法得到真传,但没能继承他的狂草,思来也是性格使然。怀素曾向颜真卿学习笔法。据《藏真帖》说:“所恨不与张颠长史相识,近于洛下,偶逢颜尚书真卿自云,颇传长史笔法,闻斯八法,若有所得也。”怀素向颜真卿求教才知道,真正的笔法存在于自然界中。怀素虽然没得到张旭的直接传授,但间接地从颜真卿处得到张旭笔法的核心思想——“道法自然”。自然万物的演变蕴藏着狂草书法的真谛!
庄子所提倡的“道”是天道,是效法自然的“道”,主张顺从“天道”,摒弃人性中那些“伪”的杂质,从而与天地相通。庄子这种“道法自然”思想,与怀素在日常生活与草书创作中“师法自然”的思想是一致的。《僧怀素传》中有一段怀素与颜真卿关于草书的讨论:
颜太师真卿以怀素为同学邬兵曹弟子,问之曰:“夫草书于师授之外,须自得之。张长史睹孤蓬、惊沙之外,见公孙大娘剑器舞,始得低昂回翔之状。未知邬兵曹有之乎?”
怀素对曰:“似古钗脚,为草书竖牵之极。”颜公于是倘佯而笑,经数月不言其书。
怀素又辞之去,颜公曰:“师竖牵学古钗脚,何如屋漏痕?”
素抱颜公脚,唱叹久之。颜公徐问之曰:“师亦有自得之乎?”
对曰:“贫道观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夏云因风变化,乃无常势,又无壁坼之路,一一自然。”
这段对话虽然不长,却非常经典地反映了怀素作书“道法自然”,从大自然的变化中悟得草书真髓的特征。
草书并非人人都能写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书家的勤奋和秉性。怀素是天才,同时也非常勤奋。《僧怀素传》中说,他小时候家里穷,买不起纸张,为习字也想尽了办法,他制作了一块漆盘,以漆盘代纸,以至把漆盘都写穿了。后来他觉得漆盘不适合书写,就在寺院附近的一块荒地上种植上万株芭蕉树,因住处触目皆为蕉林,故称之为“绿天庵”。怀素把叶子剥下来,用来练习书法。由于他夜以继日不停地书写,老芭蕉叶子剥得不多了,就舍不得再剥,于是带上笔墨干脆站在芭蕉树前对着叶子写,他顶着烈日,冒着严寒,写完一处换个地方,习书不辍。另将写坏的笔头埋在一起,名为“笔冢”。怀素虽是僧人,其实不是在中国佛教史中有地位的高僧,而是书法史中的名僧。
怀素之所以常常能够进入书法创作的忘我状态,在于有合适的媒介。怀素一生崇尚精神自由,借酒提神,洒脱不羁,逍遥处世,这无疑也受到庄子“逍遥处世”一说的启发。《金壶记》记载怀素“一日九醉”,常常处在“醉仙”的世界里。怀素是一个僧人,但同时他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酒鬼,他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陆羽说他“饮酒以养性,草书以畅志”,他在《食鱼帖》中自谓:“老僧在长沙食鱼,及来长安城中,多食肉,又为常流所笑,深为不便。”他只要一时兴起,吃肉喝酒写字全凭心情,什么清规戒律早就到了九霄云外,“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书法是他的生活,酒是他书法的灵魂,据说有人问怀素关于书法的奥秘,回答只有一个字——酒。唐代诗人张谓说“怀素作书非得百杯以后才能进佳境”,此话并不夸张。怀素一日九醉,九醉之中的毛笔在颠狂横扫,横扫下是中国传统墨色的神奇线条的激越纵横。这种由一个和尚所创造的神奇的线条世界,只能在开放的盛唐和怀素那种个性特点的完全结合下才能产生。在怀素的书法作品中,所表现的是草书寄寓酒的恣意与癫狂,“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
怀素具有“超脱自在,不为物累”的性格,任性“贵生”,追求个性自由。学识渊博,能为诗文,却没有以学入仕的念头。虽然身处佛门,然不专心“经禅”,一切清规戒律对他来说连形式也没有,摆设也不是,号称“只读经书不参禅”。芩旦宗《书评》说:“怀素闲逸,故能翩翩如真仙。”怀素崇尚“圣人不凝滞于物”,从这点来说,他的性格中,更多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了道家的特点。所以,怀素一旦进入创作状态,便纵情声色,理性退居其次,内心张扬才是首务,“忽然绝叫三五声”“驰毫骤墨列奔驷,满座失声看不及。心手相师势转奇,诡形怪状翻合宜。人人细问此中妙,怀素自言初不知”“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恍恍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怀素醉后狂若无人的创作状态,酣畅淋漓,他只要饮酒兴起,就像贯休在《观怀素草书歌》中所说的“醉来把笔如猛虎,粉墙素屏不问主”。寺院的墙壁上、衣服上、器皿上、木板上、荷叶上,但凡是他自己觉得能写的地方他都写。他也为此任性付出了代价,由于他整天颠颠狂狂,“乱写乱画”,几次被逐出寺院。他的这种不受拘束的性格,无意识地反映出了他自由不羁的道家特性。因此,怀素作为一个佛门中人,精神上却同庄子的道家思想是相融相通的。
怀素的创作状态充分见证了道家精神。因为喜欢喝酒,且每饮必醉,醉后辄挥毫作书,因为性格的狂放,不受约束,作书最易进入“天人合一”的“忘我”状态。怀素年轻时名声就很大,朱逵慕名赶到衡阳拜访怀素,真实感受了怀素的书风,曾作诗:“衡阳客舍来相访,连饮百杯神转王。”“笔下唯看激电流,字成只畏盘龙走,怪状崩腾若转蓬,飞丝历乱如回风。”其狂草代表作《自叙帖》自始至终随着感情波动跌宕起伏,情到舒缓处,便显现一种静态之美,“初疑轻烟似古松”;激越处,便显现一种天力神威之美,“笔下唯看激电流,字成只畏盘龙走”。从美学角度看,既有柔韧之美,“寒猿饮水撼枯藤”,又有力量之美,“壮士拔山伸劲铁”。从笔画来看,线条中锋运笔,如锥画沙,如印印泥。其笔画倾向于瘦细,劲健疏朗。从章法布局上看,行线摆动,大小参差,字字勾连,气息不断。写到感情激越处,雷电交加,奔矢坠石,随手万变。其大开大合,大起大落,让观者根本看不到一个一个的字,而是舞动着的优美的线条,真正是大象无形,把大醉后的“张狂忘我,天人合一”体现得淋漓尽致。通观《自叙帖》,其疏处计白当黑,清爽劲健,密处水泼不进、风吹不过,“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脉通于隔行”,整体大气磅礴,妙趣天成。我想,怀素创作《自叙帖》时,一定是酒酣欲仙,濡毫泼墨,舞之蹈之,大呼小叫。肯定如“庄周梦蝶”,沉入化境。肯定是心手相适,到了“忘我”的境界!欣赏起来如听音乐,舒缓激越此起彼伏,如看舞蹈,柔美劲健忽来忽往,千百年来,让无数书者如醉如痴,如癫如狂,难以自拔,无以释怀而又无法超越!
在书法史中,怀素和他的草书名作《自叙帖》被谈论了一千多年,见证了怀素不囿于尘俗,不囿于佛门清规,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怀素信笔成书,随手万变,不落俗套。他的师承可以追溯到张芝,比起张芝来他又无比狂放,他学张旭却不似张旭,使他悟得了独特的东西,“以狂继颠”,发展了张旭的草书。在书法史上,怀素无疑是一个成功者。其之所以能成功,正是他这种追求自由、颠狂不羁的性格特点,不自觉地隐寓了庄子的道家精神,也正是由于他这种具有庄子的“见独”特质,成就了他的旷世书风。如果怀素谨守规矩,如果怀素不是旷世奇颠,必定难以创作出横扫千载的盖世“狂草”。所以说,怀素虽寄身佛门,但其精神世界深处却闪耀着道家思想的光辉。
免责申明:
免责申明:
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书法报网立场。

- 联系我们
- 咨询电话:027-65380795
- 书法报互联网(湖北)股份有限公司 网站简介
-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街水果湖横路7号4楼01室
- 关注我们
- 微信公众号:shufabao-net
- 邮箱:shufabaonet@163.com
- 中国书法第一融媒体平台